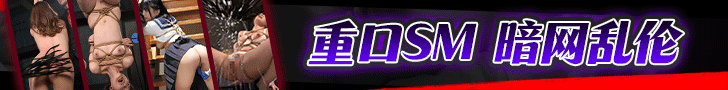我低头把衬衫纽扣重新系好了。
不知道是否错觉,刚才徐宙斯走过来的时候,我总觉得他的眼神有几秒扎到了我身上,害得我现在脊背都凉嗖嗖的。
赛表的事暂时就这样了,我挑了几个冷门的项目专攻,奖杯能拿到一个算一个,最起码让我的手以后少受点罪。
我把这几天晚上打篮球的时间腾出来,和体育组的人挤在一起拉练。
累是真的累,好几次我回家后倒头就睡着了,但爽也是真的爽,那种自由自在操场上挥汗的感觉,能发泄完一整天的闷火。
我想要不
是我还点艺术天赋的话,我真想听沈宇的话转到体育部。
我回家问我爸,能不能又学美术又学体育,双管齐下,这样考大学更有保障。
我爸乌黑着眼圈从一堆画稿里抬头,他最近正接了一个油画修复的活儿,整日整夜都泡在美术室里,连徐叔也敲不开他的门。
只有我,我爸的亲宝贝儿,才有资格挤进这间无处下脚的套房里。
“可以。”我爸点头,对我的前程发展向来很随意,“要不干脆花点钱去国外读个野鸡大学。”
“那不行。”我和我爸说,“我想考a大。”
“那爸帮不到你了。”我爸摊手,“这不是花钱就能解决的事儿。”
是啊。连我爸都这样说了。
能和徐宙斯再读同一所大学真的很难。
我有点难过。
按照徐宙斯想要摆脱我的心理,一旦他去了外地读书,我就很难再见到他了。
如果让我四年都见不到徐宙斯,那我就要死了。
“爸,你为什么不和徐叔结婚啊?”
我想蹿倒我爸和徐叔领证,这样我和徐宙斯就是名义上的兄弟了,搞不好还有机会住在一个屋檐下。
我爸手里的美工刀抖了一下,险些戳穿了桌子上油画布。
他抬头看我,表情有一瞬的疑惑,“安安不是你曾说过不想我们结婚的吗?”
“我?”我比他还疑惑,“我什么时候说过?”
我爸就认真回忆了一下,他问我还记不记得我十岁那年发的一场高烧。
一连烧了三四天,吓得他当时以为我要变傻了。
那是徐宙斯妈妈去世后的第四年。
徐叔在某次国际画展上向我爸求了婚,他们计划在瑞典登记领证,再办个小型的户外婚礼,就算是把这阴差阳错的一辈子定下来了。
我才十岁而已,整天只想着早点放学回家看动画片,压根不想去管他们大人之间的事。
但徐宙斯比我早熟很多,心思也深,得到消息的他分外不高兴。
阴郁了两天后,他趁着我爸和徐叔在国外,就把我带到了他的家里。
徐宙斯和以前一样先是陪我看了一会儿动画片,还允许我窝在他的怀里打手柄游戏。
他握着我的手去摇方向杆,将游戏画面里的赛车开得轰轰响,轮胎摩擦着地面溅起星星点点的火花。
那个年纪的小男生似乎都喜欢和大哥哥玩,我也不例外,徐宙斯在我眼里好像什么都会,什么都很厉害。
几把游戏打下来,我兴奋地搂着他脖子直叫哥哥,丝毫没有注意到他按键时的手指骨节用力到发白,明显是在借着打游戏来宣泄自己内心的怒火。
他趁我黏他的时候,把我揽在怀里问我,“安安,你爸和我爸要结婚了,你高兴吗?”
“高兴!”我毫不犹豫地回答,“这样我每天都可以和哥哥你一起打游戏了。”
闻言,徐宙斯笑了,十二岁的他刚刚有了少年模样,笑时眼睫弯弯的,脸蛋线条还很青涩。
但他粉红嘴唇里说出的话,就不是那么动听了。
“你不觉得恶心吗?”他把我拉出他的怀抱,“霍安,两个男人结婚你就有两个爸爸了。”
“在学校填家庭成员表时,你同学要是问你,两个爸爸是怎么生出来你的,你要怎么回答?”
“我、我就说我是捡来的啊……”他咄咄逼人的问话,让我有了一丝窘迫。
“也对,”徐宙斯的目光一下子变冷了,“你本来就是捡来的野杂种,没爸没妈,所以你不在乎跟着谁过日子。”
听到仰慕的大哥哥说我是野杂种没爸没妈,我小小的自尊心受挫,不由得也恼怒起来。
我把游戏机摔在他身上,冲着他大喊,“等徐叔和我爸结婚,他就是我爸爸了!”
“你也没爸没妈了!你妈早就死了!”
徐宙斯几乎是瞬间就从沙发上弹跳起来,他重重一巴掌甩在我脸上,打得我耳朵嗡嗡作响摔在了地毯上。
徐宙斯又扑过来和我扭打在一起,他像只疯狗一样恨不得把我撕碎,我用力踢他踹他,他仍旧死死压在我身上。
我也不服输,伸手去挠他的脸,但我手臂太短了,只在他的锁骨处抓出了好几道血印子。
“你还有脸提我妈,”他咬着牙低吼,“我没妈是谁害得?”
他掐我的脖子,“霍博文永远别想和徐赭结婚!你也永远只是个野杂种!”
徐宙斯从小就是这么疯批,他对我和我爸的恨意永远不会随着时间而淡化。
他打够了我,就把我拖到了二楼拐角一个小房间里,那里的家具铺满了白布,只有徐宙斯妈妈的遗照挂在墙上。
他强迫我对着照片方位跪下,他把我的头狠狠磕在地板上。
“说,”徐宙斯一字一句,“说霍博文永远别想和徐赭结婚,说你永远只能做个野杂种。”
我不说,他就又狠
狠掐我的脖子,在濒临窒息中,我憋了很久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。
徐宙斯漠视我的眼泪,但还是松开了手,他起身从外面拉下电闸,把我反锁在了这间房里。
处处都是浓稠得化不开的黑暗,我又哭又叫,拍打着房门,外头没有一丝动静。
我害怕死了,脑海里总会浮现徐宙斯妈妈的样子,她在照片里温温柔柔的模样,突然就变得阴森可怖。
她好像会说话,一直在我耳边重复着说我是个野杂种,说霍博文和徐赭永远不可以结婚。
那天的记忆到这里就很模糊了。
我不知道在房间里待了多久。
我好像昏昏沉沉陷入了一个梦里,梦里有谁终于把我背了出来,穿过长长的走廊,拐进了我熟悉的客房。
那人费劲地把我扔在了大床上,替我脱了外套和鞋袜,凉凉软软的手掌贴在我的额头上。
我不知道我在胡乱说些什么,一直嘴巴说个不停,就有人握住了我的手指,攥得很紧。
等我完全清醒的时候,已经是躺在医院病床上了。
我爸正拉着我的手和我说,不结婚了,爸爸不结婚了,别吓我了,安安。
他见我睁眼,就把我抱在怀里一摇一晃地轻声哄我,我们安安不是野杂种,是爸爸的心肝宝贝命根子。
我趴在我爸的肩膀上,看到病房门口有身影一晃,还穿着小学校服的徐宙斯转身离开了。
他背挺得很直,肩膀瘦削,手里还拎着一个大书包,像是放学后偷溜过来的样子。
夕阳的光辉穿过走廊窗户照在了他的身上,竟然给了我一种徐宙斯很孤单的错觉。
不知道为什么,我突然就不怪他了。
我爸当时还以为我是在学校遭受校园暴力了。
因为我在昏睡中一直反反复复说着自己是野杂种,说自己没爸没妈,还说两个男人结婚好恶心,我不要我爸和徐叔结婚。
他守在床边听着我说这些刻薄刮心的话,看着我脸上青青紫紫的痕迹心疼死了。
等我病好了点后,他就愤怒地找去了我们学校,谁知问了一圈后,听到的都是我平日里在学校怎么欺负别人。
我爸郁闷地回家,他也试图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,但我死活不愿再提,只装成记不得的样子,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。
说到这里,我爸又若有所思的看了我一眼,“其实我当初有怀疑过是宙斯。”
“啊?”我有点心虚的闪躲视线,“怎么会想到他……”
“也是,从小到大宙斯都是很疼你的。”我爸弯唇笑了笑,继而又说了一件让我震惊的事。
“你被我们送去医院的时候,他还坐在车后座上偷偷流眼泪。”
流眼泪?
徐宙斯流眼泪?
我震惊了。
他可是那种在他妈葬礼上都没哭过的人。
我连忙追问我爸,“他、他哭了?……他怎么会哭??您没看错吧?”
“他就坐我旁边,我怎么会看错?”
我爸又叹了口气,“宙斯这孩子就是心思太重了,嘴硬心软。”
我脑海里一下子就浮现徐宙斯十二岁时的模样,额发软软的,眼瞳漆黑,他面朝着车窗外的夜景默默流眼泪,很倔强又很脆弱。
这样一想,我忍不住塌下了肩膀垂头丧气,“爸啊,你不应该告诉我这些的。”
他妈的。
我又想要好好怜爱徐宙斯了。